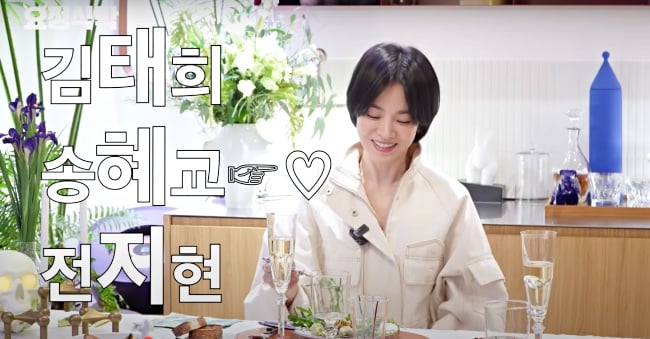《只有她知道》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三
寡婦
我聽得到她走過小徑的聲音,沉重的高跟鞋腳步聲。她就要走到門邊,卻停下腳步來把臉上的頭髮撫開。打扮得不錯,大鈕扣外套,底下是得體的洋裝,眼鏡擺在頭上。不是耶和華見證人,更不是工黨成員,肯定是記者,但不是普通的記者。她是今天來訪的第二名記者,本週第四位,今天才禮拜三。我敢說,她肯定會說:「不好意思必須在這麼令人難過的時候打擾妳。」他們都會這麼說,然後擺出一張蠢臉,好像他們在乎一樣。
我要等著她按第兩次門鈴。早上的男人沒有再按一次,有些人顯然連嘗試都覺得煩。他們的手指一離開門鈴後,就直接轉身走人,用最快的速度走下小徑,連忙回到車上開走。他們會告訴主管,他們敲過門了,但她不在家。真是可悲。
她按了兩次電鈴,然後用力叩叩叩地敲門,好像警察的敲門法。她發現我躲在蕾絲窗簾旁邊的間隙看她,然後她露出了燦爛的微笑。好萊塢式的微笑,我媽都這麼說。接著,她又敲起門來。
我開門的時候,她拿著擺在門口的牛奶瓶,說:「妳不是想把這個留在外頭吧?會壞掉的。我可以進來嗎?妳煮水了嗎?」
我不能呼吸,更別說講話了。她又笑了起來,歪著頭,說:「我是凱特。凱特.華特斯,我是《每日郵報》的記者。」
「我——」我正要開口,卻忽然發現她沒有問。
「泰勒太太,我曉得妳是誰。」她說,沒說出來的弦外之音是:「妳就是報導本身。」她反而說:「咱們別站在外頭。」不知怎麼著,她一邊講話,就莫名奇妙進屋了。
事情變化太快,我訝異到說不出話來,她把我的靜默當成默許,便拿著牛奶走進廚房,替我泡茶。我跟著她過去,廚房不大,我們算是有點擠在一起,她則忙著在茶壺裡注水,然後一一打開我的櫥櫃,尋找杯子與糖。我就傻傻站在哪裡,看著所有的動作。
她聊起這個空間。「妳家廚房實在清新可愛,真希望我的廚房也像這樣。這裡是你們自己裝潢的嗎?」
我感覺好像是在跟朋友聊天。我原本不是這麼想的,我是在跟記者講話啊。我以為感覺會像接受警方盤查問話一樣。那可真是一場磨難,訊問。那是我丈夫格倫說的,但不知怎麼著,感覺沒那麼差。
我說:「對,我們選了白色的門跟紅色的把手,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清爽。」我站在自己家裡,跟一名記者聊我家廚房。格倫肯定會氣死。
她說:「從這裡出去,對吧?」然後,我打開前往客廳的門。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希望她在此,我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有什麼感覺。現在抗議感覺不太對,她只是坐下來跟我喝茶聊天而已。說來好笑,我還滿享受這種關注了。我猜這是因為格倫不在了,我一個人在家裡感覺有點寂寞。
而她似乎掌控著大局,這樣真的很好,有人可以再次替我做主。我原本已經開始焦慮,自己必須處理所有的大小事,但凱特.華特斯說她會把一切都處理好。
她說,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的人生故事說給她聽。
我的人生故事?她才不是真的想了解我。她爬上我家小徑才不是為了琴.泰勒,她只想知道關於他的真相,關於格倫,我的丈夫。
你知道,我的丈夫三週前過世了。就在森寶利超市外頭遭到公車撞死。他在那裡才一分鐘,抱怨我該買什麼樣的早餐穀片,然後,下一分鐘,他就橫死街頭。他們說他的頭部受到重創,總之就是死了。路人跑來跑去,想要找毯子蓋起來,人行道上還有鮮血,不算很多。他應該會覺得慶幸,因為他最討厭一團亂的場景。
每個人都很好心,企圖擋住我的視線,不讓我看到他的屍體,但我實在沒辦法告訴他們,我其實很慶幸他死了。再也不用看他胡搞瞎搞了。
第二章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三
寡婦
當然,警察趕到了醫院。就連偵緝督察鮑勃.史巴克茲都趕來急診室談格倫的事情。
我沒有對他解釋,也沒有跟任何人講話。告訴他們,沒什麼好說的,我太傷心了,沒辦法講話,還哭了一下。
至今三年多,鮑勃.史巴克茲督察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份,但我覺得,說不定他會跟著格倫你一起消失。
我沒有對凱特.華特斯說這些。她坐在客廳裡的另一張扶手椅上,握著馬克杯裡的茶,抖動著腳。
「琴。」她說,我發現她不再稱呼我為泰勒太太了。「對妳來說,這個禮拜一定很恐怖。妳經歷了那麼多。」
我什麼話都沒說,只是盯著自己的大腿看。她才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沒有人知道,真的,我沒有辦法告訴任何人。格倫說這樣最好。
我們坐著,不發一語,然後,她換成別的方法。她站起身來,從壁爐架上拿起我們的一張照片,畫面裡的我們對著某個東西歡笑。
「妳看起來好年輕。」她說:「這是你們結婚前拍的?」
我點點頭。
「你們認識很久才結婚嗎?是在學校認識的嗎?」
「不,我們不是同學,我們是在公車站邂逅的。」我告訴她:「他好帥,會逗我笑。我那時才十七歲,在格林威治的髮廊當學徒,他在銀行工作,看起來年紀比較大,會穿西裝,還有好看的鞋子。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講得好像什麼愛情小說一樣,凱特.華特斯把這些話當成寶,在筆記本上奮筆疾書。她從小小的鏡片上看了看我,對我點點頭,一副她也心有戚戚焉的感覺一樣,但她可唬不了我。
其實呢,一開始,格倫看起來可不是浪漫的人。我們約會都找燈光昏暗的地方,好比說電影院、他的福特車後座、公園,我們沒什麼時間交談,但我記得他第一次說愛我的情景。我渾身刺痛,好像我感覺得到自己每一寸的皮膚一樣。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覺得自己真正活著。我急著告訴他,我也愛他,我吃不好也睡不著,滿腦子都是他。
我在家裡閒晃的時候,我媽說我是「上癮」了。我不確定這個「上癮」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想和格倫一直在一起,那個時候,他也是這麼想的。我覺得媽媽有點吃醋。她太仰賴我了。
「琴妮,她太依靠妳了。」格倫說:「帶著女兒到處跑,這樣不健康。」
我企圖解釋媽媽不敢一個人出門的狀況,但格倫說她實在太自私了。
他很保護我,他會選距離吧台最遠的座位,理由是「怕妳覺得太吵」。他還會在餐廳替我點餐,這樣我就能吃到不一樣的東西,他會說:「琴妮,妳會喜歡這個,試試看吧。」於是我乖乖聽話,有時新口味的確不錯,有時卻不怎麼樣,不好吃的時候我不會說出來,免得傷他的心。如果我跟他意見相左,他會陷入沉默,我不喜歡這樣,我會覺得自己好像讓他失望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和格倫一樣的人交往過,他曉得自己的人生該怎麼走。其他男孩就真的只是男孩而已。
兩年後,格倫向我求婚了。他並沒有單膝下跪,只有緊緊抱著我,說:「琴妮,妳是我的。我們屬於彼此⋯⋯我們結婚吧。」
那個時候,他也贏得了媽媽的信任。他會帶花來給她,說那是「給我生命裡另一位重要女人的小禮物」,這話可以把媽逗得樂不可支,他會跟媽聊她喜歡的《加冕街》和《皇室成員》這兩齣連續劇。媽說我很幸運,說格倫能夠讓我走出自己的小框框,他可能會讓我有所成就。媽媽看得出來他會照顧我,他也的確非常照顧我。
「那個時候,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凱特.華特斯問我,還靠向前鼓勵我多說一點。她所謂的「那個時候」指的是所有的壞事還沒有發生之前。
「噢,他是個很可愛的人,很肉麻,恨不得成天跟我黏在一起。」我說:「他動不動就送我花和禮物,說我是他的唯一。這一切都讓我招架不住,我那時才十七歲。」
她喜歡這段話,連忙以醜得好笑的字跡記錄下來,然後抬頭。我掩住笑意。我察覺到歇斯底里的情緒湧了上來,但表現出來的樣子卻像在啜泣,她伸手過來輕撫我的手臂。
「別難過。」她說:「一切都結束了。」
是啊,警察不會再來了,格倫不會回來了,他也不會繼續「胡搞瞎搞」了。
我想不起來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用這四個字的,一切應該是在我能夠具體稱呼那到底是什麼之前就發生了。我那時忙著表現出我們婚姻最完美的一面,我們的婚姻從查爾頓之家的婚禮開始。
爸媽覺得我十九歲就結婚,年紀太小了,但我們說服了他們,好啦,格倫說服了他們。他非常堅定,全心全意愛著我,最後老爸終於答應,我們開了一瓶義大利的藍布魯斯科汽泡酒慶祝。
爸媽為了婚禮,花了大把鈔票,因為我是他們的獨生女,而且我花了前半輩子的時間跟老媽一起研究新娘雜誌上的照片,幻想我的大喜之日。我的大喜之日。我居然能把全部的生命通通維繫在這一個日子上頭。格倫沒有什麼意見。
「那是妳負責的。」他如是說,然後大笑起來。
他講得好像他也有負責的事情一樣,我猜那應該指的是他的工作,主要賺錢養家的人是他,他會說:「琴妮,我知道這樣聽起來很老套,但我想好好照顧妳。妳年紀還小,我們還有美好的遠大前程。」
他總是有遠大夢想,他每次講這些東西的時候,都聽起來非常激動。他要成為分行經理,然後他就要離職,自己創業,自己當老闆,賺很多錢。我可以想見他穿著上好的西裝,旁邊還有秘書,開著豪華大車。而我,我就會在他身邊。他會說:「琴妮,不要改變。我就喜歡妳這樣。」
於是,我們買了位於十二號的房子,婚禮後就搬進去。多年後,我們還在這裡。
房子前面有個院子,但我們鋪了小石子上去,格倫說:「這樣就省得除草了。」我喜歡草坪,但格倫喜歡簡單乾淨的風格。我們一開始一起住的時候,實在很辛苦,因為我有點不修邊幅。在娘家的時候,我媽永遠都可以在我床上那團亂糟糟的東西裡找到髒盤子跟湊不成對的襪子。要是格倫知道,他肯定會當場暴斃。
我現在想起他來,有天晚上,我們吃完飯後,我用手把食物殘渣掃到地上,他咬牙切齒,瞇起眼睛。我根本沒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我一定想都沒想就掃了幾百次,但我再也不敢了。他在這種事情上對我來說算是助益,他會教我事情該怎麼做,才能維持好這個家,他喜歡把家裡維持得好好的。
早期的時候,格倫會告訴我銀行工作裡的大小事,他的責任是什麼,後輩如何仰賴他,工作人員之間開著什麼玩笑,老闆有多討厭琴妮。(他以為自己最棒)還會介紹跟他一起共事的人。內部辦公室的喬伊跟麗茲,另一名行員史考特,膚質很差,怎樣都會臉紅,還有阿梅,不斷犯錯的實習生。我喜歡聽他說,喜歡聽他講他的世界。
(待續)
【延伸閱讀】
好書不寂寞,妞書僮來陪你看看書
如果妞妞們喜歡《控制》,那你會愛上這本書!費歐娜.巴頓小心翼翼的揭開恐怖罪行、令人窒息的婚姻背後的黑暗故事,描繪出伴侶為了繼續婚姻關係而自欺欺人的謊言,結局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本文摘自《只有她知道》

出版社:皇冠文化
作者:費歐娜.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