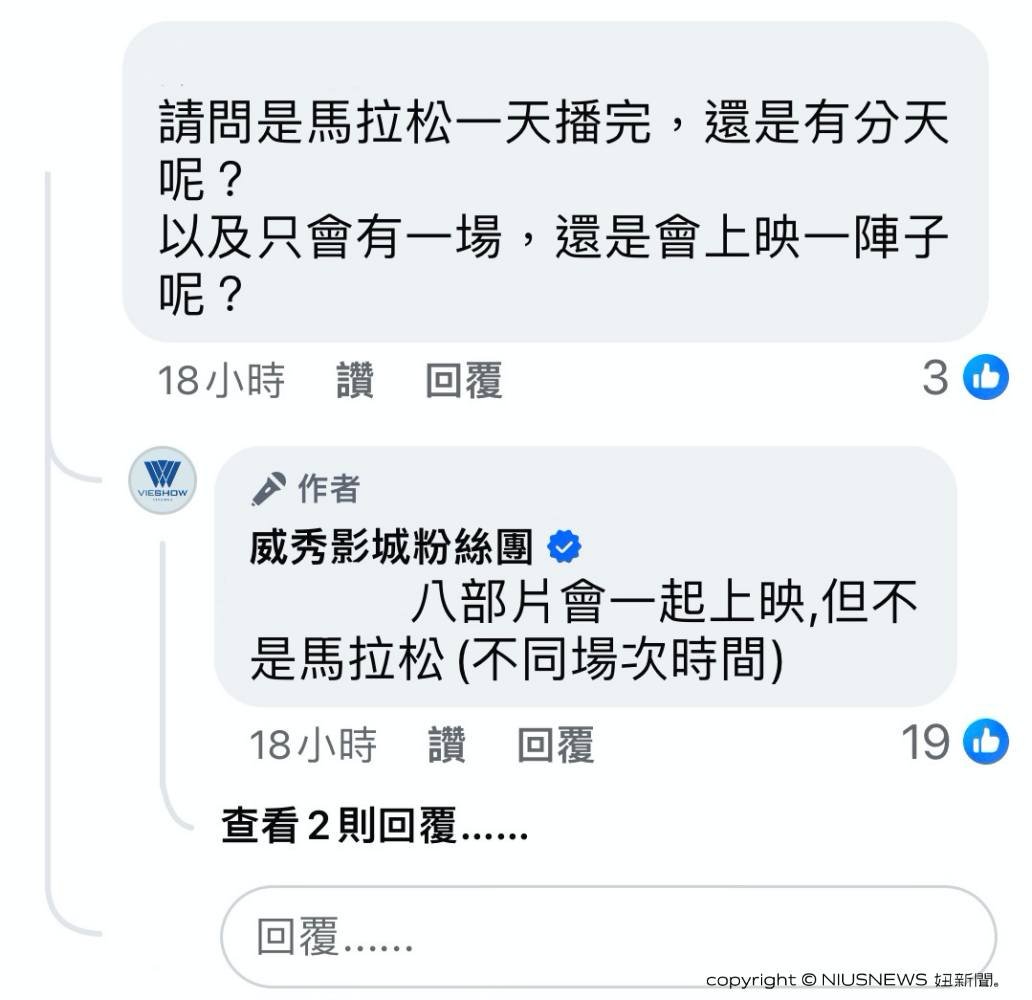《因為愛,我們呼吸》
第一章
可惡的女人老是亂動他的東西。他只要在客廳將靴子亂脫或把太陽眼鏡放在咖啡桌上,她就總會把東西拿到「該放的地方」。是誰說家裡她最大的?要是他想要在廚房餐桌正中間拉一坨臭死人的大便,那坨屎就得留在那裡,除非他自己動手移走。
我那把該死的槍去哪兒了?
「蘿希!」喬從臥室大喊。
他看了一下時間:上午七點零五分。要是他不趕快出門,那就會趕不上點名了,但沒找到槍,他就哪裡都去不了。
仔細想想。最近太過匆忙,他好難仔細想。加上這裡比地獄還要熱上好幾千度。六月的氣溫讓人熱得喘不過氣,整個禮拜都將近攝氏三十度,晚上偶爾才會降下來。這種天氣太難睡了。家裡的空氣悶死人,昨天就困在室內的熱度和濕度,但今天又變得更悶。窗戶是打開了,但一點兒幫助也沒有。穿在防彈背心裡的白色Hanes T恤都黏在他的背上了,讓他氣得要死。他明明才剛沖過澡,現在就可以再沖一次。
仔細想想。他沖完澡,穿好衣服──褲子、T恤、防彈背心、襪子、靴子、手槍腰帶。接著他把槍從保險櫃中拿出來,扳機鎖解開,之後呢?他轉頭看右臀,槍不在那兒。他其實根本不用看,就可以從重量感覺到槍不在那兒。彈匣袋、手銬、防身噴霧、對講機、警棍都在,就是槍不在。
槍不在保險櫃裡,不在床頭櫃上,不在床頭櫃最上層的抽屜裡,也不在還沒整理的床上。他看了一下蘿希的梳妝臺,除了象牙色小飾巾上的聖母瑪利亞以外,什麼都沒有,而聖母瑪利亞顯然幫不上忙。
聖安東尼啊,那把該死的槍到底在哪兒?
他累壞了。他昨晚到體育館周邊負責指揮交通。可惡的大賈斯汀演唱會拖得好晚。他是很累,那又怎樣?他已經累好幾年了。他無法想像自己會累到這麼不小心把裝滿子彈的槍隨便亂放。喬有很多同事都對自己的武器越來越得意,但他從來沒有。
他衝過走廊,經過兩間臥室,將頭探進家裡唯一的浴室。槍不在那兒。他衝進廚房將雙手放在屁股上,習慣性地用右手掌跟找尋槍把的位置。
他們家四個還沒沖澡、還沒梳理、睡眼惺忪的青少年坐在廚房的小餐桌旁吃早餐──幾盤沒有完全煎熟的培根、稀稀的炒蛋和烤焦的白吐司。一如往常。喬掃視了廚房,發現他的手槍。他那把裝滿子彈的手槍,就放在水槽旁邊的佛麥卡塑膠貼面芥末黃流理臺上。
「早啊,爸。」老么凱蒂說。她雖然笑著,但有點兒不好意思,感覺到事情不太對勁。
喬沒有理凱蒂。他拿起克拉克手槍,穩妥地放進手槍皮套內,把怒氣全對準蘿希。
「妳把我的槍拿到這裡幹麼?」
「你在說什麼?」蘿希說,她沒有穿內衣,穿著粉色背心、短褲,赤腳站在爐子旁邊。
「妳老是把我的東西亂放。」喬說。
「我從來沒有動過你的槍。」蘿希反駁他說。
蘿希是個身高一五二公分,體重頂多四十五公斤的小個子。喬也沒有特別高大。他穿上警靴之後身高一七五,但大家都覺得他看起來更高,大概是因為他的胸膛寬大、手臂健壯、聲音低沉沙啞的關係。三十六歲的他有點兒啤酒肚,但以他這年紀來說還算保養得不錯,畢竟他得經常坐在巡邏車裡。他平常愛開玩笑、很好相處,可以說是很溫和的人,但就算是他在笑的時候,藍眼中還是有股閃爍,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派的硬漢。沒有人敢鬧喬,除了蘿希以外。
她說的沒錯。她從來沒有動過喬的槍。即使他已經當了這麼多年的警察,她還是不習慣家裡有槍枝,即使槍總是在保險箱或是他床頭櫃最上層的抽屜裡,就算已經關保險,或是在他的右臀上。但今天不一樣。
「那槍他媽的怎麼會跑到這裡來?」他指著水槽旁邊問。
「你說話注意一點兒。」她說。
他看向四個孩子,他們都不吃了,正在看戲。他瞇著眼看派翠克。老天愛他,但這十六歲的小子蠢得要死。儘管他之前一再教育這些小孩不能亂動他的槍,但像他這種笨蛋就是會做這種事。
「那是你們哪一個人做的?」
他們全都盯著他,沒人出聲。查爾斯頓心照不宣的沉默是吧?
「是誰拿了我的槍,把它放在水槽旁邊的?」他厲聲問道。這時不能再不開口了。
「不是我,爸爸。」梅根說。
「也不是我。」凱蒂說。
「不是我。」小喬說。
「我也沒拿。」派翠克說。
就跟他逮捕過的每一個嫌犯會說的一樣。大家都是他媽的聖人就對了。孩子們全都抬頭看著他,眨眼等著。派翠克將韌韌的培根塞進嘴裡開始嚼了起來。
「吃點早餐再出門吧,喬。」蘿希說。
再吃早餐就會遲到了。他來不及吃都是因為剛才在找那把某人亂拿,丟在廚房流理臺的該死手槍。他已經遲到了,覺得快失去控制,而且好熱,太熱了。擁擠的廚房裡,空氣太悶,難以呼吸,彷彿爐上的熱氣和六個人加上天氣,都促使他體內就快燒開的東西燒得更旺。
他點名要遲到了,比喬小五歲的小隊長瑞克.麥當勞又會再跟他約談一次,甚至向上呈報。他光想到會有多丟臉,無法吞忍,怒氣終於爆發。
他抓起爐上的鐵鍋把,側身往旁邊一打,在離凱蒂腦袋不遠的牆上打出一個不小的洞,接著掉在油氈地板上,又砰了一聲。煎培根的深棕色油渣在雛菊花色的壁紙上滴了下來,有如傷口迸出的血。
孩子們都瞪大眼睛,不敢說話。蘿希一句話也沒說,站著不動。喬衝出廚房,跑過窄廊,走進浴室。他的心跳得好快,頭腦漲熱,太熱了。他用冷水沖濕臉和頭髮,再用擦手巾擦乾。
他得立刻出門了,就是現在,但鏡中的他有個東西拉著不讓他走。
他的眼睛。
他的瞳孔放大,因為腎上腺素的關係變得又黑又寬,像鯊魚眼一樣,但不是這個。是他眼睛裡透露出的神情讓他走不了。瘋狂、茫然、滿是怒火。他的母親。
他小時候總是被這種精神錯亂的凝視嚇到。他看著鏡子,明明已經遲到了,卻忍不住緊盯著母親可怕的雙眸──她以前躺在州立醫院的精神病房裡,什麼都做不了,不發一語、憔悴不堪、瘋狂、等死的時候,就會這樣看著他。
他母親眼中已經死了二十五年的惡魔,現在就在浴室的鏡子裡盯著他看。
七年後
第二章
這是個涼爽的週日早晨,喬在遛狗,蘿希上教堂去了。他以前會在休假時跟老婆和孩子們一起去,但自從凱蒂受洗之後,他就不再去了。現在只有蘿希會去,但她覺得那些可悲又罪惡的人都令她作嘔。喬很喜歡傳統,可是對於只在每七週半才能輪休到週休二日,六年來沒有跟家人共度過耶誕早晨的人來說,這是個很倒楣的特質。要是他有空,還是會參加耶誕夜的彌撒和復活節,不過他已經受夠每週的聖禮了。
也不是他不相信神、天堂和地獄、善與惡、對與錯。羞恥心還是會左右他每天的決定。神看得見你。神知道你在想什麼。神愛你,但要是你搞砸了,你就會下煉獄。他所有的青春,修女都拿著那些妄想的信條敲擊他的後腦袋,從眉心打進去。現在這些想法還在裡頭轉啊轉,沒有出口。
但神一定知道喬是個好人。要是祂不知道,那每週一小時在聖方濟各教堂的跪地、坐下或站立也救不了喬不朽的靈魂。
他還是信神,可是讓他失去信心的是天主教堂這個組織。有太多神父哄騙太多小男孩,太多主教和樞機主教,甚至連教宗本人都掩蓋了整起可恥的亂事。喬並不是女權主義者,但要是問他,他會認為這些人可是藐視女性權益。首先是不能節育這件事。拜託,這真的是耶穌要求的嗎?要是蘿希沒吃避孕藥,他們現在大概已經有一打小孩了,她也肯定一隻腳踏進墳墓了。天佑現代醫學啊。
這就是他們養狗的原因。生完凱蒂之後,喬告訴蘿希不要再生了,四個已經夠了。蘿希在他們高中畢業那個夏天就懷了小喬(他們很幸運,外射的方法管用到那時才中標),所以他們就先有後婚,十九歲之前就當了爹娘。小喬和派翠克長得如出一轍,兩人相隔十一個月出生。梅根繼派翠克之後十五個月誕生,而凱蒂在梅根之後十八個月呱呱落地。
小孩長大上學之後,生活就變得輕鬆許多,但前幾年的情況慘不忍睹。他記得出門前送飛吻向蘿希說再見,她卻不理會,喬得留她一個人在家照顧四個五歲以下的孩子,其中三個還穿著尿布。他很感恩自己有正當理由離開家裡,但每天也都擔心著老婆自己一個人顧孩子,撐不到他下班回家。喬真的會想像她做出可怕的事情,他的工作經驗和同儕親眼看見的故事助長了他最深的恐懼。一般人要是被逼到極限,就會做出瘋狂的蠢事。蘿希大概十年來都沒有好好睡過一覺了,而且他們的孩子可是難搞得很。他們都還活著根本是奇蹟。
蘿希一開始並不同意內野計畫(喬這麼稱呼)。她根本瘋了,竟然還想生。她想要替歐布萊恩名單至少再增加個投手跟捕手。她有六個哥哥,是家裡最小的妹妹,即使她現在很少見到哥哥,還是喜歡當大家庭裡的一分子。
但喬下定決心,事情就這麼決定。他才不會退讓。這是生平第一次他拒絕做愛,除非蘿希答應他節育。那三個月可真夠難熬的。他本來已經決定好從今以後都要在洗澡時自己解決那檔事,直到有天發現他的枕頭上有個圓形的扁盒。打開後,他發現有一圈的藥丸,七顆的量已經空了。蘿希違背神的旨意,就這樣結束了這場冷戰。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扒光她的衣服。
但要是她不能再生,她就要養狗。很公平。接著她就從動物收容所抱了一隻西施回家。喬覺得她是故意要惹他生氣才選了西施,這是她表達最終決定權的方式。喬是波士頓警察耶,她嘛幫幫忙。要是養拉布拉多或伯恩山犬或是秋田也比較像樣。他是答應可以養狗,養隻真正的狗,可不是神經質的小老鼠。他很不高興。
蘿希將狗取名悅姿,至少讓他能多接受這隻雜種狗一點兒。喬以前痛恨自己出門遛悅姿,總讓他感覺自己像個娘娘腔。但後來他就放寬心了。悅姿很乖,喬也夠有男子氣概,讓查爾斯頓的人看到他在遛西施也沒關係,只要蘿希不給小狗穿上愚蠢的毛衣就好。
他喜歡在沒執勤的時候在鎮上到處散步。即使當地人都知道他是警察,他還是會把槍藏在沒有紮的衣服裡;穿著制服、佩戴警徽讓他很像顯眼的目標,現在褪去硬漢警察的身分之後,他覺得卸下重擔。他一直都是警察,但下班後,他就只是在附近遛狗的普通人。這種感覺很好。
這裡的每個人都說這裡是「鎮上」,但查爾斯頓(Charlestown)並非真的鎮,說起來也不是市。這是個波士頓的街坊,算起來還是個小地方而已,只有查爾斯河和神祕河之間塞下的一平方英里地。不過,就像每個愛爾蘭男人講到男子氣概時都會說的:尺寸不夠,就用個性補足。
喬長大的查爾斯頓被非正式地分成兩個街坊。山丘底下的部分是貧窮的愛爾蘭人居住的地方,而山丘頂端的聖方濟各教堂附近都住著比較有點兒錢的愛爾蘭人。丘頂的人可以說跟丘底的人一樣窮,或許很多方面來說他們也是如此,但大眾的看法是他們的日子比較好過。現在這裡的人還是這樣想。
社區裡也有一些黑人家庭,和北邊溢出來的義大利人,但除此之外,查爾斯頓就是一個充滿許多勞動階級人口的地方,有很多家庭住在緊簇的殖民時期三層房屋內。每一個本地人都認識鎮上的每一個人。要是喬小時候做了過分的事(經常發生),他就會聽到有人從門廊和窗戶大喊:喬瑟夫.歐布萊恩!我看到你了,我要跟你媽說!以前的人不需要叫警察。比起警察,小孩子更怕父母。喬最怕的就是他媽媽。
二十年前,查爾斯頓都是本地人。但這裡近年來變化很大。喬和悅姿慢慢爬上山丘步入柯迪斯街,彷彿他們經過那個轉角就踏進另一個郵遞區號的地區。這條街上的住宅都已經全部重新整修,不是磚房就是塗成帶有歷史氣息、獲准使用的顏色。現在門換新,窗戶也換了,變成整整齊齊一排排的花兒在銅製的窗框上盛開,人行道上也有漂亮的煤燈點綴。喬繼續往上爬的時候,他看了一下停在旁邊的車款──賓士、BMW、Volvo。這裡根本就像是他媽的燈塔山了。
歡迎來到外地人大入侵。喬也不怪他們來。查爾斯頓的位置非常好──傍河,上了贊金橋(Zakim Bridge)就能進波士頓市中心,過托賓橋(Tobin Bridge)能到北邊,走隧道可以到南岸線,搭個精巧的渡輪就能到昆西市場(Faneuil Hall)。所以外地人開始湧進這裡,帶著他們的高階白領工作和鼓鼓的錢包,買房地產,讓這一區連帶地變得高級起來。
但外地人通常不會久留。他們剛來的時候都是雙薪無子的小家庭。接著,幾年後,可能會生一個孩子,或生兩個恰恰好。等老大到了要上幼稚園的年紀,他們就會搬去郊區。
所以打從一開始就是短暫的而已,他們不在乎住哪兒,不像那些知道自己會在一個地方住到進棺材的人。外地人不會去青年會當志工或是去少棒隊當教練,而且大多數人都是長老教會、一神論派,或是素食者,或是些奇奇怪怪的身分,所以他們不支持這裡的天主教會,這也是為什麼聖凱瑟琳教堂關了。他們不會真正地融入社群。
但最大的問題是,外地人讓查爾斯頓變成其他人也想來的地方,他們拉抬了房市。現在只有有錢人才能住在查爾斯頓了。這裡土生土長的鎮民有千百種,但除非去搶銀行,否則可沒人稱得上有錢。
喬是查爾斯頓的第三代愛爾蘭人。他的祖父派翠克.札維耶.歐布萊恩自一九三六年從愛爾蘭搬來,在海軍造船廠擔任裝卸工人,以每週四十美元薪水養一家十口。喬的父親法蘭西斯也在海軍造船廠負責修補船隻,工作雖苦但薪水不錯。喬的警察薪水也不至於讓一家人吃土,都還過得去就是了。他們在這裡從不覺得窮。不過大部分的下一代鎮民,不管是做哪一行,肯定無法在這裡生活下去。真是太可惜了。
他經過一棟獨立式殖民風格房屋,前門放著一塊「出售」招牌,是極少數有前院的房子,所以喬試著猜測賣方出價有多誇張的高。他們現在住的房子是喬的父親買的,是位在丘底的一棟三樓屋,一九六三年以一萬美金購入。上週兩條街外有棟類似的三樓屋以整整一百萬售出。每次他想到這點,就覺得實在太誇張了。有時候喬會跟蘿希討論把家賣掉,這種興高采烈又不切實際的對話,聽起來就像在討論哪天中樂透要怎麼辦一樣。
喬會去買輛新車,黑色保時捷。蘿希不開車,但她會去買一堆新衣、新鞋和貨真價實的珠寶。
但這樣的話他們要住哪兒?他們才不要搬去有大片土地的郊區豪宅,這樣他還得買除草機。蘿希的哥哥全都住在離波士頓至少四十五分鐘路程的鄉下小鎮,每個週末似乎都忙著拔雜草、護根,或是耗費體力的農務。誰想要那樣啊?如果他們要搬去郊區,那他得離開波士頓警局才行。這不可能。不過說實在的,他也不可能在這裡開那種車,目標太明顯了。所以他沒有要買新車,蘿希繼續戴假珠寶也沒關係,畢竟有誰想要成天擔心被搶或被偷呢?因此儘管每次他們都興沖沖地討論起這件事,但總會繞一大圈,又穩穩地回到原點。他們夫妻都很愛住在這裡,就算全世界的金銀財寶都拿來,他們也不會想搬家,就連搬去南區也不要。
他們很幸運能繼承這棟三樓房。喬的父親九年前過世時,將房子留給喬和他唯一的姊姊瑪姬。他們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才找到她。瑪姬一直都是喬的相反,她高中畢業後就下定決心立刻離開,再也不回來查爾斯頓。喬後來發現她搬去加州南部,離了婚,無子女,也不想要那棟房子。喬也理解。
他和蘿希住在一樓,二十三歲的派翠克也跟他們一起住。他們的長子小喬和媳婦柯琳住在二樓。凱蒂和梅根同住三樓。除了派翠克之外,每個小孩都會付房租,不過不多,比市價低很多,只是要讓他們負點責任而已,也能減輕房貸的負擔。他們為了讓四個孩子念教區的學校,重新貸款了幾次。這件事難歸難,但喬絕不可能讓孩子們搭車去多徹斯特或羅克斯伯里念書。
喬轉了彎,決定穿過多赫提公園。週日上午這種懶洋洋的時候,查爾斯頓十分安靜。克勞格帝泳池沒開,籃球場也空無一人。小孩子如果不是在教堂,就是在睡覺。除了偶爾經過的車聲,唯一的聲響只有悅姿的狗牌的叮噹聲,以及喬的前口袋中的零錢,像曲子一樣撞得作響。
如其所料,喬看見八十三歲的麥可.墨菲坐在樹蔭下遠處的長椅上。他拿著拐杖和裝有過期麵包的棕色袋子餵鳥。他會整天坐在那兒看著人來人往,留意當地發生的事,每天都是,除非天氣特別糟糕。他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了。
「你今天好嗎,市長?」喬問道。
大家都叫墨菲「市長」。
「比大部分女人要好多了。」墨菲說。
「沒錯。」喬笑道,雖然問同樣的問題,喬每三次都會收到市長這個一字不差的答案。
「第一夫人好嗎?」墨菲問道。
墨菲都叫喬「總統先生」。他在幾百年前,因為老甘迺迪夫婦的小名音似喬與蘿希,就開始以「甘迺迪先生」這個綽號稱呼喬,接著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就由父傳子,藐視真正的美國政治史,後來甘迺迪先生的稱呼變成了(小甘迺迪)總統先生。當然,蘿希也變成第一夫人。
「很好,她在教堂替我禱告。」
「那肯定要一陣子了。」
「是啊,再見,市長。」
喬繼續走在小路上,從滿是工業筒倉的這座丘上看向遠方的風景,以及神祕河另一端的埃弗里特造船廠。很多人會覺得這風景沒什麼特別的,甚至看了生厭。此處可能找不到畫家帶著畫架來作畫,但喬看到一種城市之美。
他下陡坡了,走階梯而不是旋梯,卻不知怎麼突然踩空了,只看到一面天空。在他還沒回過神用手撐地之前,已經滑下整整三階樓梯。他自己爬起來,坐在地上,這時就已經感覺到脊椎突出的地方肯定滿是糟糕的瘀青了。他轉過身看階梯,覺得一定是路上有棍子、石頭或是不穩的階梯之類的障礙讓他踩空。但什麼都沒有。他看向最頂階,望向四周的公園,看著下方的地面。至少沒人目睹。
悅姿噴著氣,搖動尾巴,急著想繼續走。
「等一下,悅姿。」
喬舉起雙手,檢查手肘,兩邊都破皮流血了。他揮掉碎石和血,慢慢站起來。
他到底是怎樣跌倒的?一定是他的爛膝蓋。幾年前他在華倫街上追一個入侵行竊嫌犯時,扭傷膝蓋了。磚塊人行道看起來漂亮,但可是凹凸不平、彎彎曲曲的,跑起來是折磨,特別是晚上。從那之後,他的膝蓋就不如以往,似乎偶爾就會突然罷工。他應該去檢查一下,但他從不看醫生的。
接下來的階梯,喬走得特別小心,直到梅德福街。他決定切進去,再從高中那裡出來。蘿希應該快結束了,他現在覺得每走一步,下背就會刺痛,所以想快點回家。
他走上波克街時,一輛車在他身旁慢了下來。是唐尼.凱利,喬小時候最好的朋友。唐尼還住在這裡,是個急救員,所以喬不管上下班,都經常看到他。
「你是昨天喝太多是不是?」唐尼搖下龐帝克的車窗,笑著問他。
「啊?」喬也笑著問道。
「你怎麼一跛一跛的?」
「噢,我的背在痛。」
「要載你過去嗎,老兄?」
「不用,我沒事。」
「少來,上車吧。」
「我需要運動一下。」喬拍拍肚子說。「麥特還好嗎?」
「很好。」
「那蘿莉呢?」
「很好,大家都很好。嘿,你真的不要我載你嗎?」
「真的不用,謝謝你。」
「好吧,那我先走了。掰啦,歐布。」
「再見,唐尼。」
唐尼的車還在視線範圍內時,喬故意走得很穩、很快,但等唐尼開上山丘消失後,喬就不裝模作樣了。他步履維艱地走,每一步都好像有個隱形螺絲更深地扭進他的脊椎裡,他現在倒希望剛才搭便車了。
他回想了唐尼剛剛說他喝太多的事情。他知道那只是個無心的玩笑,但喬一直都對他的名聲與喝酒很敏感。他從來不會喝超過兩杯啤酒。好吧,有時候喝完兩杯,會再灌一份威士忌,只是想證明他是個真男人,不過就這樣,不會超過。
他的母親是個酒鬼,把自己灌進了瘋人院,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事情已經過了很久,但這種爛事會一直跟著你。大家什麼事情都不會忘,而你的出身就如你本人一樣重要。要是你媽酗酒而死,那大家多少也會期待你變成發狂的醉漢。
露絲.歐布萊恩把自己灌到死。
大家都這麼說。這是他的家族傳奇也是爛攤子。這句話不管什麼時候出現,就會緊跟著一連串的回憶,讓喬很容易感到不自在,所以他會很快轉換想法,才不會「鑽牛角尖」。紅襪隊如何?
但今天,不管是因為更有勇氣、更加成熟,或是好奇,他不知道怎麼了,就讓這句話一直跟著他上山丘。露絲.歐布萊恩把自己灌到死的。說不通啊。對,她酗酒。簡而言之,她灌酒灌到不能走路也無法好好說話。她會說很誇張的話,做很誇張的事、暴力的事。她會完全失控。當他父親再也受不了,就把她送到州立醫院了。她死時,喬才十二歲。
露絲.歐布萊恩把自己灌到死。他生平第一次有意識地發現他一直以來奉為真理的這句話,有如他出生日期一樣,可查核又假不了的事實,不可能是真的。他的母親在醫院待了五年,所以她死在醫院病床上的時候,應該是跟骨頭一樣乾枯得滴酒未沾才對啊。
說不定因為她的大腦和肝臟泡在酒精裡太多年,結果就變成糊,所以為時已晚,傷害已經造成,沒辦法醫好。她濕潤的大腦和濕軟的肝臟最終衰竭了。死因:長期飲酒。
他爬上丘頂,鬆了一口氣,準備好繼續往比較輕鬆的街道和話題邁進,偏偏他母親的死還糾纏不去。這個新理論有一點兒不太對勁。他覺得心神不寧、事有蹊蹺,就像他接獲通報處理案件時,沒人告訴他實情的感覺。他對真相有種直覺,而這不是真相。要是她不是灌到死的,也不是與酒精相關的死因,那是什麼?
他又走過三個街口,想找出更好的答案,但毫無頭緒。這件事很重要嗎?她死了,她死很久了。露絲.歐布萊恩把自己灌到死。別再想了。
他走到聖方濟各教堂時,鐘響了。他立刻就看到蘿希站在最頂階等他,喬笑了。他們十六歲開始約會時,他就覺得她是個美女,而且他真心覺得老婆年紀越大越美。四十三歲的她有著白裡透紅的肌膚,臉上有雀斑,紅褐色頭髮(這年頭要有這種髮色都要用染的了),一雙讓他至今看了還是會腳軟的綠眼睛。她是個了不起的母親,能夠忍受他的個性,根本是聖人了。他很幸運。
「妳有幫我說好話嗎?」喬問道。
「說了好幾次。」她用手指向喬灑聖水說道。
「很好,妳知道能幫上忙的我都需要。」
「你流血了嗎?」她看到他的手臂說。
「對,我跌下階梯了。我沒事。」
她握住他另一隻手,舉起手臂,發現那個手肘也擦傷流血了。
「你確定?」她問道,眼神充滿關切。
「我沒事。」他說,並緊握著她的手。「來吧,我的新娘,我們回家。」
【延伸閱讀】
本文摘自《因為愛,我們呼吸》

出版社:高寶出版
作者:莉莎.潔諾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