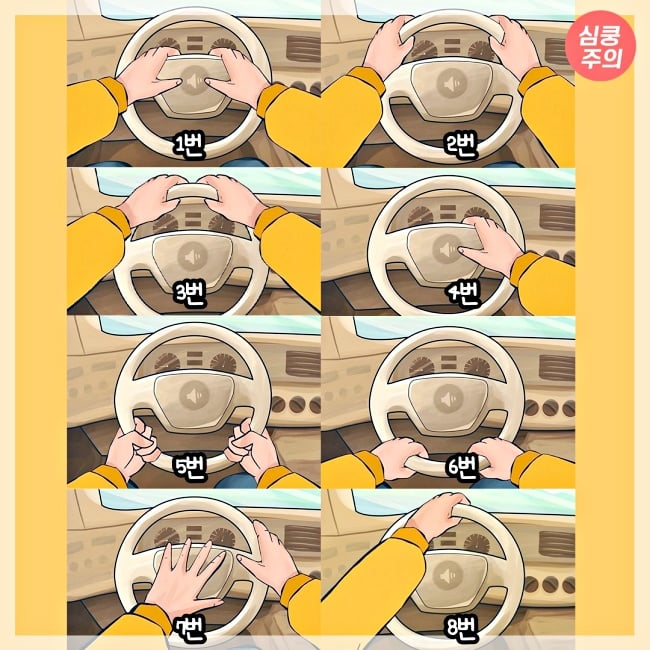我跟我自己
正在回收代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兩腿之間有種怪怪的感覺,急忙衝進廁所。我本來就覺得日子差不多到了,但我沒有記錄月經周期的習慣,只是覺得快來了的時候就開始用衛生棉,結果一天下來發現一點痕跡都沒有,就這麼浪費了一片衛生棉,也是常有的事,但這一次好像來得特別晚,讓我等得有點心焦。我脫下內褲確認,本來很擔心褲襪和褲子都弄髒了,結果發現內褲上只有透明黏滑的液體,我還伸手去摸,用拇指摩擦食指確認了觸感。我呆了好一陣子,褲子都還沒穿起來。嘆了一口氣,正想撕一小張衛生紙來擦擦額頭上的出油時,外面傳來敲門聲,這唯一的廁所隔間被打開了。是蒂芬妮……不,是杉內小姐。
杉內小姐欲言又止地盯著我一陣子才說,哎呀,不好意思,妳好像忘記鎖門了。然後給了我一個自然的笑容,猛然關上隔間的門,走出廁所。我在洗臉臺洗淨了手指,又回去繼續工作。
我曾經懷孕過幾次,都是和不同的男朋友懷的孩子,一副理所當然地製造著生命。或許我的體質特別容易受孕,去年第三次懷孕時我才開始這樣懷疑。即使懷了孩子,我從不打算結婚,也沒有深刻地思考過全身麻醉之後從我的體內消除的一個靈魂。睡意像汙染一樣從插在我左手上的針頭漸漸擴散,我如同衝下螺旋階梯似地陷入夢鄉,醒來以後,總是發現自己睡在病床上。就像小時候被你抱下車一樣,大人們靜靜地推著我的床,這裡沒有小時候感覺到的溫柔和洋溢的關愛,我也不想知道這裡有的是什麼。我清楚地意識到下腹部開了一個洞,卻感覺不到失去什麼的悲傷。葬禮自顧自地完成了。在我沒有意識的時候,工具悄悄地攪毀了一切。看到染血的衛生棉,我才發現這件事。黑白的、能握在掌心的小小超音波照片,背後寫著日期和沒有被叫過的名字。那是多麼沉重的罪孽。手術後,我睜開眼睛,在模糊的視野中把手掌打開又握緊,像是在跟天花板玩猜拳。你現在在哪裡呢?還沒成形的生命去了哪裡呢?你恨我嗎?即使我試著找尋沒有擁抱過的溫暖,也不可能得到回答,天花板不會回答,腹裡也不會。我拿起放在身邊的智慧手機一看,我到醫院已經過了六個小時,一坐起身,就感到身體某處不小心撞傷的瘀青在痛,和腹部的疼痛相比,我竟然更在意瘀青,真是奇怪。腦袋隱隱作痛,像是有什麼東西貫穿了全身,我好想趕快離開這個慘白的房間,雖然想逃,卻又不知道能逃到哪裡去。我穿好衣服,雙手合十,喃喃地說著對不起,但是沒有人會回答「我不怪妳」。這樣更叫人害怕。
沉默是最令人難受的。
回到家裡,我脫去身上的衣服,脫掉內褲,像游泳一樣在棉被上躺成大字形。我盯著斑駁剝落的薄荷巧克力色調的天花板。榻榻米的房間竟然配上這種色調的天花板,屋主的品味也未免太差了,不過坐北朝南的方位和日照充足的圓窗令我覺得非常舒適。讓使用了一天的全身肌肉放鬆之後,我拿出冰箱裡的燒酒加入汽水來喝。智嗣還沒跟我聯絡,今天大概也會很晚回來吧,我看看掛在牆上的時鐘,從丟滿整個房間的衣服所掩蓋的書堆之中抽出我不久前逛書店時亂買的一本書,漫不經心地讀起封面折口上的大綱、作者資料、出版日期,好像什麼都看不進去,這時我的意識突然飄走,好像斷線了一樣。
現在的我來說,成為大人,以及成為母親,兩者都很重要,然而這些能確切拓展未來的希望卻不存在於我的身上,我只是仗著自己還年輕,敷衍著「以後再說啦」,但這句話就像一支利箭,漸漸膨脹,最後終會變成一塊大石頭,把我壓得粉碎。我感受著酒精在我的體內滲透,揮著手臂像是要撕開平白流逝的時間,來回走在狹窄的房間內,越走越覺得腦袋發昏,腳下一個踉蹌,我倒在薄薄的墊被上。
本文摘自《凹凸》

「不管是女兒、母親,
都離不開身為「女性」的這種病──」
絹子與丈夫正幸結婚後十三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栞
,從這天起兩人便不再有魚水之歡。直到「那一天」,絹
子終於決定與丈夫告別,一個人努力將女兒拉拔長大。而
栞即使長大離家、到了二十四歲,依然被「那一天」的記
憶所綑綁,這時她竟發現男友智嗣和她的父親正幸有些相像……
廣受年輕女性好評的作者根據親身經歷而創作,既是家人
、又同樣身為女性的母親和女兒,橫跨兩代性與愛的故事
出版社:尖端
作者:紗倉真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