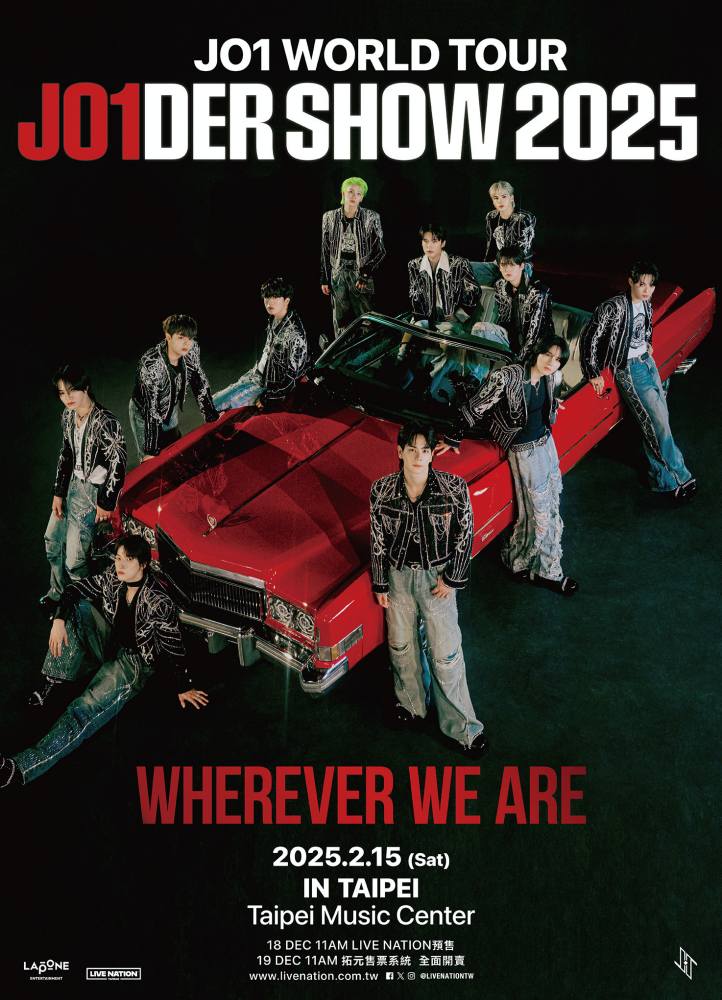(採訪當日,完成新書第一頁想寫的字。)
重寫,讓我明白自己最核心的情感
出版過兩本詩集《下雨的人》《那些最靠近你的》,陳繁齊這次寫散文。他以最習慣抒發原始自我心境的文體,圍繞著詩意旋風,再一次和讀者對話。
陳繁齊2016年在出版浪潮上展露頭角,希望未來產量是一年一本的創作,算是對自己的期望。而為什麼是一年?他語帶靦腆說:「一年是看見一個人改變的最小單位。一年,不會太細碎,也足夠改變。」
他的回答讓人深思,這個最小單位是否也適用於每一個人?
只是,這「一年一本」的期許,卻帶來一次無法言喻的衝擊。
交出文稿後,他沒想到被總編輯「退稿」了。他坦言寫了不少,但僅僅只拿出一半的量,竟然就被砍了四分之三……雖然訪問的此刻,他淡淡陳述,其實「當時非常受挫」陳繁齊不諱言,偏偏他又有一種必須征服什麼的意志力,他決定全部重寫。
在重寫的三、四個月裡,他每天下午一點開始,乖乖坐在電腦前,可能發呆什麼都沒做,可能重覆翻著筆記本,或者聽過一張又一張Spotify上的專輯,他強迫自己去面對。
創作的盲點,是一個極具殺傷力的敵人,而陳繁齊遇見了這個敵人,又殺死了這個敵人。
他以為散文就是要詳細描述細節,譬如描寫一本書頁就要極盡所能地描述所有細節──折角、破損、泛黃,甚至書名、頁數。但他忽略了這些細節後面是有情感連結的,於是被打掉重練的這一批文字,他重新挖掘躲在文字後面的那些情感。過去大學時封閉狀態中鉅細靡遺描寫細節的盲點,也並非毫無可取,那些過程等於示現了最原始的陳繁齊。
「重寫,讓我明白了自己最核心的情感。」未來是否可以一年一本的狀態未可知,但在每一部累積的作品中,他同樣期許回望時都能真心吟味自己的記錄與成長。

(第一篇以〈時差〉之名為開場,標記著整本書的框架況味。)

(新書的照片皆來自陳繁齊的攝影作品)
失眠之於我,等於寫作之於我
談到為什麼兩本詩集之後,是一本散文而不是詩?他說:「出版詩集純屬意外。只因在社群媒體上被大量分享,也被較為活躍的鋼筆寫手抄寫轉發。回頭來看,第一本詩集算是給自己的退伍禮物,而後第二本詩集隔一年出版,接下來應該要回歸自己最熟悉的文體,畢竟這個文體是寫詩之前,自己進入文字書寫的起點。」
實際上陳繁齊完全沒想到自己會出書,「作家這個職業的印象等同於吃不飽(笑)」。
陳繁齊回憶,一開始寫是國中畢業時親近朋友離世,說什麼言語都很多餘,覺得誰都無法百分百理解的狀態下,開了無名小站以鎖文隱藏的方式,每天寫,一定要寫點什麼才有活著的感覺,而後高中畢業,到了大學,他才意識到原來當時那樣天天寫,是一個出口,是某種程度的救贖。
現在有自己的理想寫作日程嗎?陳繁齊說較理想的情況是「東想一句西想一句,先記下來,擺一段時間,突然有想法了,就把他們全部組起來。很多時候讓它停留發酵是好的。直到那個情感終於擊中內心深處,或是擺得成熟了,自然會有辦法與自己做連結,完成一篇作品。」
但最奇妙的是,「睡前兩小時是最佳寫作狀態」陳繁齊彷彿說了自己的祕密般。
「那一段時間可能因為心裡已經預設要睡覺了,所以思緒很乾淨,比任何時候都要專心想。於是可能想一想之後,就起床寫下來,寫了幾百字之後又再躺回去想一想, 有時會反覆就寫個一兩千字......」但這樣的狀態不就是失眠嗎?也許「寫作」這個過程,就是含有一種習慣性失眠,能夠甘之如飴的人就能幸福享用。

(每天寫,一定要寫點什麼才有活著的感覺。)
感性是永遠的功課
在這本新書裡,讀到很多句子充滿詩意。陳繁齊在兩種文體之間遊走,彷彿詩與散文的距離,被風化了。「我在寫詩時,不需要去解釋很多,甚至可以把情節做跳躍式的安排,甚至可以只描摹感情不需描摹事件,或者只描摹事件不描摹感情。許另一種說法,就是寫詩的時候可以理所當然地藏。但對散文來說兩者是並行的,也許一方較重一方較輕,但兩者都很清楚存在,很清楚地寫下來或被讀到。」
文字成為陳繁齊意想不到的發聲工具,他承認,但用「工具」兩字太冰冷,當他為一些議題或身邊的人事物提出看法與想法時,「感性」是他永遠的功課,而這也終將成為「陳繁齊式」的風格。有讀者說因為他的文字被療癒了,這樣的說法讓他覺得意外也欣喜,向來只是圍繞著自己寫而已,竟也能被他人承接。在某些時候陳繁齊的自卑感,仍令他難以相信自己真的擁有那些能力──治療、理解他人,對他而言,都是人際關係中較為柔軟的體現。
為什麼新書書名叫《風箏落不下來》,一次在回答總編輯的提問時,他說:「風箏可以意指過去的時光,也可以直指思念,或指一種目光、一種因他人而起的改變。 落不下來,大概就是這整本書的書寫狀態。或者說,書寫過程是要讓它落下來。畢竟一起放風箏的人已經不在身邊了。」
我們期待,陳繁齊的文字再一次讓不同世代的讀者,有著溫柔的共鳴,而這共鳴不是要如何定義這位年輕的創作者,而是我們從他的文字中找到了理解的階梯,一步一步理解自己。風箏有一天會落下來,落到我們的心裡。
(詩與散文的距離,在這本書中被風化了。)
文
/
大田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