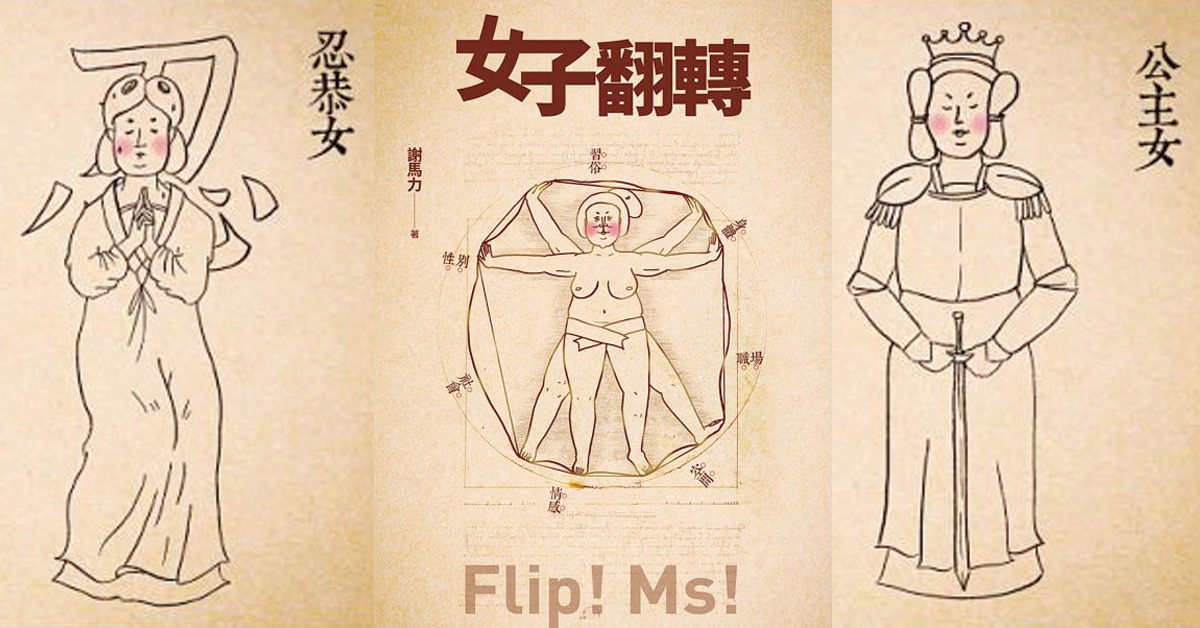《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
一九四○年的夏天,任何一通電話、一張紙條,或是一聲低語,都可能警示札賓斯基夫婦,讓他們準備接待地下軍安排的「客人」:躲躲藏藏和在輾轉逃亡途中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就像游牧民族,而非定居屯墾的住民,只是暫時停下來休息加油,再上路到不知名的目的地。長得像亞利安人,又會說德語的猶太人可以拿假證件順利地離開,但過不了關的人則會在動物園一待數年,有的住在動物園長屋內,有時多達五十人全散居在空的獸籠裡。許多客人,如汪妲,都是全家人的老朋友,安東妮娜把他們當成兩棲家族,要藏他們當然是問題,但還有誰比動物園長更適合安排合宜的偽裝?
在其他被德軍占領的國家,藏匿猶太人可能會讓你蹲大牢;而在波蘭,藏匿猶太人非但可能讓藏匿者當場被處死,而且還會牽連家人與鄰居,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責任」。雖然如此,還是有許多醫院員工讓猶太成人偽裝成護士,並下藥讓猶太兒童昏迷,再偷偷把他們用背包運送出去;或者把他們藏在一堆屍體之下,用運屍車悄悄運出去。許多波蘭基督徒都把猶太朋友藏匿了整段戰爭期間,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得減少自己的口糧,時時刻刻提心吊膽,還得挖空心思,窮於應付。只要這房裡有任何多出來的食物、不熟悉的身影,或者由櫥櫃中流洩出的呢喃低語,都可能招致左鄰右舍的懷疑,向警方密告,或是向城裡的敲詐者透露消息。被抓進牢裡的人往往在黑暗中一待多年,幾乎不可能移動,等他們最後終於出獄之時,想伸展四肢,卻已經孱弱無力,只能像木偶一樣被抬出來。
動物園未必總是客人的第一站,尤其由猶太區逃出來的,可能先在市區伊娃.柏祖斯卡(Ewa Brzuska)家待一兩天,大家都稱呼為「阿嬤」(Babcia)的伊娃是個臉色紅潤、身材矮壯的婦女,年約六十,她在塞索斯基街上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一路延伸到人行道上,一桶桶的德國泡菜和醃黃瓜就放在一簍簍的蕃茄和青菜旁,鄰居擠在店裡買東西、聊天;雖然德國軍隊的汽車修理站就在對街。每天都有一群猶太人被德軍帶到修理站來修車,阿嬤會偷偷幫他們寄信,或者在他們和家人說話時幫他們把風。堆得高高的馬鈴薯可以讓由猶太區來的小朋友躲在後面,一九四二年,她家成了地下軍組織的辦公室。她把各式身分證件、出生證明、錢和糧票藏在醃黃瓜和泡菜桶下;把危險分子的出版品收在貯藏室裡;並且經常收容猶太人臨時過夜,大部分的猶太人接著都會轉往動物園躲藏。
安東妮娜很少弄得清楚什麼時候客人會上門,或者他們由哪裡來,一切都由姜恩籌畫聯繫。
天黑之後,札賓斯基家也依規定,在窗戶上掛起黑紙,但白天裡,這棟原本只供一家人住的兩層樓房卻像蜂巢一樣忙碌不已。有這麼多符合規定的住客─管家、保母、老師、姻親、朋友和寵物─一屋子人影和喧鬧似乎再正常不過。這房子太過明顯,就像展示箱一樣, 四周只有幾叢低矮的灌木,幾株長成的大樹和招牌的落地大窗。姜恩刻意這樣安排,在視線所及一清二楚的情景,正符合越公開的地方越不惹人注目的座右銘。
在不知名也無法預期的人潮來來去去的流動之中,的確很難看出誰是客人,更難說出誰什麼時候不在那裡。然而這樣的祕密行動卻意味著如履薄冰的生活,必須默默地評斷每一種噪音,追蹤每一個陰影。某個聲音是否和這棟房屋不斷的變化協調?屋裡的人都像得了妄想症一般,而這也是對永遠不斷的危險唯一正常的反應,住客全都成了偷偷摸摸的武術大師:躡手躡腳、靜止不動、偽裝假冒、轉移目標、啞劇。有的客人躲藏起來,有的則猶豫徬徨,唯有入夜時分,才敢自由地在屋裡走動。
這麼多人同住,也意味著安東妮娜有更多雜務。她原本就要照顧大家庭,牲畜、雞、兔子要養;菜園裡的蕃茄和菜豆要種;每天要烤麵包;醃漬蜜餞蔬菜、還要把糖煮水果裝罐。
波蘭人已經習慣占領區的驚嚇,前一刻還風平浪靜,後一刻卻飛沙走石,讓他們四散奔逃。每天早上,他們在黑暗中醒來,不知道今天要面對什麼樣的命運,也許是憂傷,也許不免被捕。她會不會是其中一分子?安東妮娜不禁疑惑,他們消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正好置身德軍隨意選中的電車或教堂裡;他們封住出口,殺死裡面所有的人,為了他們真正受到或想像中的侮辱報仇。
家事,不論多麼單調重覆,至少是熟悉的動作,熟悉、無害、自動。不斷保持警戒只會教人筋疲力竭,感官知覺無法完全放鬆,大腦的看守人不斷地在可能的碼頭逡巡,探看陰影,聆聽危險,直到意識成了自己的懺悔者和囚犯。在死刑的國度,在晨光或星辰的移轉隱藏在百葉窗簾之後,時間也變了形,喪失了它的靈活性, 安東妮娜寫道,她的日子更加朝生暮死,「就像肥皂泡泡一般脆弱」。
先前安東妮娜偶爾會陪著姜恩去拜訪知名的昆蟲學家西蒙.唐納本博士(Szymon Tenenbaum),他的牙醫太太羅妮亞(Lonia),和女兒伊瑞娜(Irena)。姜恩和西蒙小時上同一所學校,結為好友,常一起在溝裡爬,翻找石頭,那時西蒙就已經是昆蟲狂,長得像聖甲蟲的金龜子是他的最愛,是他的太陽神,也是他最專門的生物。長大之後,他開始四處旅行,趁著餘暇收集昆蟲,還出版了關於地中海巴利亞利群島(Balearic Islands)甲蟲的五大冊專書,躋身頂尖的昆蟲學者。在學年中,他擔任一所猶太高中的校長,但一到暑假,比亞洛維察森林裡甲蟲聚集,一段空樹幹就像藏著一座小小的龐貝古城,這時西蒙就來此搜集許多罕見的標本。姜恩本人也喜歡甲蟲,曾作過大規模的蟑螂研究。
即使在猶太區,西蒙依舊繼續寫文章、收集昆蟲,把他的獵物釘在玻璃蓋下的棕色木盒子裡,不過在納粹剛命猶太人搬到猶太區時,西蒙擔心不知該如何保存他那些寶貴的大型收藏,因此曾問姜恩可否把它們藏在他家。幸好一九三九年黨衛軍突襲動物園,搶走兩百本寶貴書籍、許多顯微鏡及其他設備時,沒注意唐納本近五十萬昆蟲樣本的收藏。
札賓斯基和唐納本家在戰時益形親密,日常生活的困苦使他們交情更深。安東妮娜在備忘錄中寫道,戰爭不只會使人分隔,反而會加深友誼,點燃愛火,每一次的握手都開啟了新門,或者操縱了新的命運。而就因為他們和唐納本家的友誼,因緣巧合之下,他們認識了一個讓姜恩與猶太區關係更鞏固的關鍵人物,只是這人自己卻毫不知情。
一九四一年夏的一個周日上午,安東妮娜看到一輛豪華轎車停在門前,一名塊頭很大的德國人由車裡鑽了出來,他還來不及按門鈴,她就跑到起居室的客廳,大彈起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輕歌劇《美女海倫》(La Belle Hélène )中的〈去,去,去克里特!〉一曲,這是要所有客人躲進藏身之所,保持安靜的暗號。安東妮娜對作曲家的選擇,說明了她的個性,和當時家裡的氣氛。
姜恩去開了門。
「前動物園長是不是住在這裡?」一名陌生人問。
過了片刻,那人進了屋。
「我叫齊格勒(Ziegler),」他說,並自我介紹他是華沙猶太區勞工局長,這個單位照理說是為猶太區裡外失業者找工作的單位,但實際上,他們卻只把最有技術的勞工送往戰備工廠,如埃森的克魯柏鋼鐵工廠,對於其他因納粹統治而處於半失業狀態,往往有病在身的勞工,則沒有多少幫助。
「我想看看動物園了不起的昆蟲收藏,唐納本博士捐贈的收藏,」齊格勒說。他聽到安東妮娜輕快的琴聲,不禁開懷微笑說:「這裡氣氛多麼活潑!」
姜恩引他到起居室。「是啊,我們家很愛好音樂,我們很喜歡奧芬巴哈。」
齊格勒似乎有點不情願地說道:「嗯,呃,奧芬巴哈是個膚淺的作曲家,不過我們得承認,整體說來,猶太人是很有才華的民族。 」
姜恩和安東妮娜焦灼地互看對方一眼。齊格勒怎麼知道昆蟲收藏的事?姜恩後來回想,他當時想:「我想今天就是末日了!」齊格勒看到他們困惑的模樣說:「你們一定吃了一驚,讓我解釋一下。唐納本博士授權讓我來參觀他的昆蟲收藏,你們應該有幫他保管。」
姜恩和安東妮娜戒慎恐懼地聽著。判斷是否危險,就像拆除隨時會引爆的炸彈一樣,成了一門技術—只要聲音的一點顫抖,判斷的一點錯誤,世界就會爆炸。齊格勒是什麼意思?只要他一聲令下,大可直接取走昆蟲收藏,沒有人會阻止他,因此他們沒有必要撒謊說自己是為唐納本保管他的收藏品。他們知道非得迅速回答,以免對方疑心。
「哦,對,」姜恩刻意顯得漫不經心似的說:「唐納本博士在搬去猶太區以前,把收藏品留給我們,因為我們這裡很乾燥,有中央暖氣;而他的收藏品很容易就會在潮濕寒冷的房間裡受損。」
齊格勒會意地點點頭:「沒錯,我也這麼想,」他還說,他也是昆蟲學者,業餘的,他覺得昆蟲實在教人著迷。他就是因此和唐納本博士結緣,不過湊巧的是,唐納本的太太羅妮亞正好就是他的牙醫。
「我經常去看西蒙.唐納本,」他興致高昂地說,「有時我們開我的車到華沙郊區,他在涵洞和陰溝裡找昆蟲,他是很傑出的科學家。」
(待續)
【延伸閱讀】
好書不寂寞,妞書僮陪你看看書
「不畏懼,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這本書真的會碰觸你每一根神經,跟著一起憤怒、一起顫抖、一起感動。
本文摘自《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黛安‧艾克曼